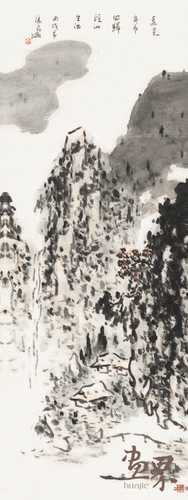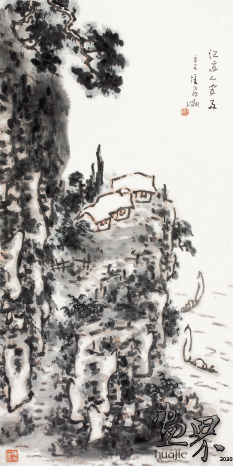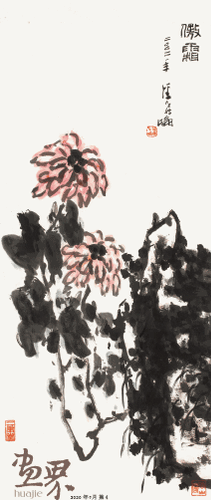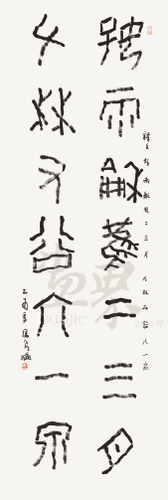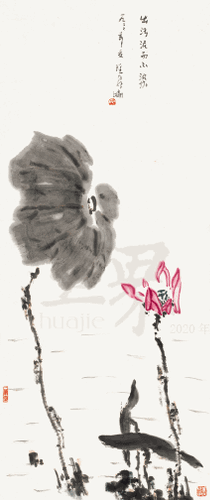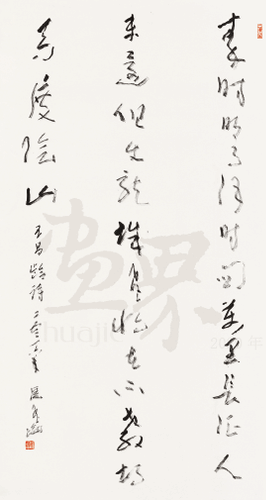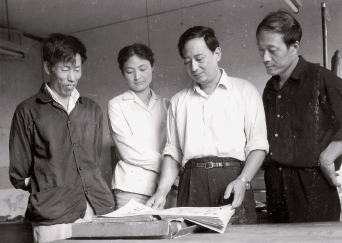首頁>書畫>畫界雜志>2020年第四期
潘飛侖:一筆堂中藝理深
溪山圖-188×70cm-2006年-潘飛侖
江邊人家-138×69cm-2001年-潘飛侖
落日余暉-180×97cm-2014年-潘飛侖
山居圖-137×68cm-1987年-潘飛侖
1962年,我有幸考入浙江美術學院時,潘飛侖兄已是五年級的大師兄了。在學業成熟的老大哥中,飛侖兄那簡潔挺勁的筆墨,饒有潘天壽院長的意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這次有緣拜讀到飛侖兄以“一筆堂”命名的《畫語》,我并不感到奇怪。他的“一筆”,簡約而深厚,就是他書畫藝術的根本所在。
飛侖兄是幸運的,他是潘天壽先生的寧海同鄉,桑梓之情使他得以常聆教誨;更幸運的是,潘先生為他設計了未來的藝術之旅—使學人物畫的他“聽了潘天壽先生意見,我改學了山水”。
對于潘天壽先生來說,山水畫不是主業,但他以偏師獨出的魄力使簡筆山水出以冷峻雄健的氣局,成就不在其花鳥之后。這樣的格局自然深深地影響著飛侖兄。但是,視山水為主業的飛侖兄,并沒有簡單地重復潘先生的路數,而是一往情深地筑基于傳統山水的學習中:“我學山水畫,先后研習宋代的巨然、李成、董源,元代的黃公望、倪云林,明代的沈周,清代的王石谷、石溪、石濤、八大山人以及近代的黃賓虹、潘天壽等。”正是在充分理解黃、潘兩位大師鑒古開今的源淵所在之后的取法乎上,使他不但清醒地認識到“畫法從老師中來,又要不同于老師,學不像,拉開距離,自立門戶”的重要性。但他也深知,只有從繁入簡,才是一條必經之路,因此他認真地這樣實踐著:“在美院學習時,方向是簡筆,疏密對比強烈,然后逐步進入繁筆……,晚年從繁入簡。”這正是一位專業山水畫家必須經歷的過程。晚年的黃賓虹正是以這樣的理念,進行著具有“神品”內涵的繁筆山水向具有“逸品”性格的簡筆山水演化的實踐。從繁到簡,的確有一個質的飛躍—是對筆墨脫盡繁華、只存本真的一種修為。這也是我對飛侖兄“一筆觀”的一種詮釋吧。
石濤在他的《苦瓜和尚畫語錄》中開宗明義地說:“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我的理解是,中國畫造型、造境、抒情、暢神的最基本元素即來自“一畫”的運動之功,在運動中演化萬物而得以再造人的理解之境。所以,只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一筆”的生命無限性,才能從根本上把握到中國畫的本質(其實書法亦同此理)。我認為飛侖兄所表示的“一筆”即是石濤“乃自我立”的“一畫”之說。
“一筆”的功能如此神妙,是從什么途徑臻于此境的?飛侖兄的實踐證明了我一貫的想法:筆法固然是書畫家主體精神的跡化,但從技法層面上講,以唐楷為代表的“提按轉折”技法加上以先秦篆籀為代表的“萬毫齊力”技法,兩者相融即是用筆“千古不易”的存在理由。因此,飛侖兄的“一筆”之功,正得力于金石、書法藝術的長久磨礪和熏陶。他回憶:“我十歲開始刻圖章……,進美院后轉入正軌,在舊貨店里買來許多破章,磨了再刻。從秦漢、西泠八家、徽派、皖派及現代的齊白石、吳昌碩。課桌上擺滿了圖章。到目前,也有幾千方。”可見積功頗深。由此我想到黃賓虹的一段話:“道、咸之間,考核精確,遠勝前人。中國畫者,亦于此際復興。”所謂“考核精確”,除了對傳統經典花更大力氣進行考據整理鉤沉之外,又對大量出土的三代古器、漢魏碑版作了新的觀照和臨寫。特別是其中金石學的興起,為書畫家們扭轉日趨萎靡的館閣書體和文人畫風找到了一味強筋健骨的靈丹妙藥。換個角度來說,正是書壇碑學(包括篆刻)的興起,才使中國的文人畫從道、咸時期開始振興。而真正體現這個效果的,還是由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這一輩人完成的。潘天壽先生自然深受影響,于是,追隨潘先生的飛侖兄也自覺地接受了這個影響。正是對金石、書法致力深厚,才使諸樂三先生對飛侖兄的繪畫作出了“有金石氣,書法味”的評價。這其實就是對飛侖兄參悟“一筆”真諦的肯定。
有了這樣性能的“一筆”,不僅有造型造境的生發功能,更有抒情暢神的傳遞作用。于是,他的山水不因簡筆而寡淡無味,相反,使人們體味到看盡繁華后的真水無香。
按照飛侖兄的水平和資歷,早就應該與他的同學們一樣,至少名滿省內外了,但他卻甘于寂寞:“學畫要耐得住寂寞,等于要坐十年冷板凳。古代不少書畫家,關門不出,或隱居山林,求得清靜,專心研究書畫,故成就很高。現在這種人太少了。”“冷落,被人遺忘,并非壞事,恰恰有更多的時間可用在研究畫畫上,是個好機會。”這真是達者之見。的確,實用與表現密不可分的書法和娛人與娛己難以厘清的文人畫,規定了學習的方法必然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當然是指在攀登藝術高峰過程中的社會影響和經濟回報;而“有所不為”,則是指在前進過程中的反省、思考和學習,甘心遠離當下可以得到的名利收獲。然而,不少書畫家往往難以拒絕接踵而來的實際利益而不愿“有所不為”,從而導致書畫家雖江郎才盡而猶“顧盼自雄”,藝術生命其實早已結束。飛侖兄清醒地體察到這個帶有規律性的現實,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定位在“有創造力”的畫家上面。他深切地認識到,那些喧鬧的“藝外之功”都是對這個定位的傷害。他進一步認為,“創造力”的取得不僅僅是閉門造車般的用功,而要如前輩老師所提倡的那樣,書畫家在追求“三絕”、“四全”之外,更應該做到“六合”。他說:“‘六合’就是詩、書、畫、印、畫史、畫論融合在一起。”對于一位以弘揚文人畫傳統為己任的畫家來說,飛侖兄的這個主張無疑是非常有見識的。如果更多的書畫家能按照這個知識結構來磨礪自己,那么蘇東坡所說的“腹有詩書氣自華”,必會潤澤到其腕底的筆墨進而提升其藝術品位。但是,這樣的知識結構也必然要求藝術家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工作態度。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黃賓虹的一段話:“我邦畫者,不友海內外通人以擴聞見,以展覽欺愚眾,以高值駭嚇富豪,此顏習齋大儒所謂詩文書畫天下四蠹,誠痛乎其言之也。”其實,“展覽”和“高值”在現代社會是合理的存在,而書畫作品本身應該具有的價值不應該名不副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求書畫家具有創造作品真價值的品質和本領。飛侖兄的這本《一筆堂畫語》的精神內核即在這里。最后,將我的讀后之感濃縮為四句話以結束此文:“冷淡生涯不怨天,揚帆墨海自翩翩。自從探得驪珠后,一筆縱橫六合全。”
(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員、浙江省書協顧問)
傲-霜-138×59cm-2002年-潘飛侖
“好雨左林”篆書聯-273×70cm-2005年-潘飛侖
出污泥而不染-173×70cm-1999年-潘飛侖
昌齡詩(草書)-180×97cm-2016年-潘飛侖![]()
十萬墨跡(白文)5×5cm 潘飛侖篆刻
豪放不羈(朱文)7.5×7cm 潘飛侖篆刻
畫畫有聲(白文)5×5cm 潘飛侖篆刻
1985年王星記扇廠,左起潘飛侖、錢小純、朱豹卿、曾宓
潘飛侖:(1935—2019),生于浙江寧海。1963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為潘天壽入室弟子,生前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2019年,潘飛侖逝世后,其家屬整理山水、花鳥、篆刻等遺作共141件及部分文獻捐贈給浙江美術館,為答謝捐贈,2020年,浙江美術館舉辦了“一筆如椽—潘飛侖書畫展”,呈現這位藝術家不斷探索的藝術精神及出色的成就。
責任編輯:張月霞
文章來源:《畫界》2020年7月第4期
編輯:畫界-邢志敏
關鍵詞:潘飛侖 篆刻 書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