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yè)>文化>閱讀
四十多年過(guò)去,薩義德的《東方學(xué)》仍然訴說(shuō)著當(dāng)下
提起薩義德,大部分人第一時(shí)間聯(lián)想到的便是《東方學(xué)》。可以說(shuō),“東方學(xué)”作為薩義德最有影響力的概念,自其在1978年成書(shū)出版之后,成為“西方”認(rèn)識(shí)“東方”的框架,也為后殖民理論研究開(kāi)辟出一塊寬闊土壤。
提起薩義德,大部分人第一時(shí)間聯(lián)想到的便是《東方學(xué)》。可以說(shuō),“東方學(xué)”作為薩義德最有影響力的概念,自其在1978年成書(shū)出版之后,成為“西方”認(rèn)識(shí)“東方”的框架,也為后殖民理論研究開(kāi)辟出一塊寬闊土壤。
小半個(gè)世紀(jì)過(guò)去了,圍繞東方學(xué)的爭(zhēng)辯與解讀依舊不斷。這也多少掩蔽了薩義德的其他思想,譬如文本的“在世性”,也譬如他身上所混合的世界主義的人文主義等。在新近出版的《導(dǎo)讀薩義德》一書(shū)中,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張理解薩義德關(guān)鍵思想的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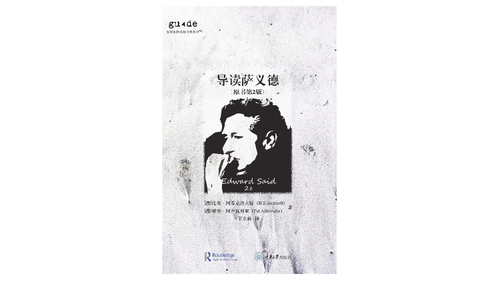
《導(dǎo)讀薩義德(原書(shū)第2版)》,[澳]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澳]帕爾·阿盧瓦利亞 著,王立秋 譯,
拜德雅 | 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12月。
原作者 | [澳]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澳]帕爾·阿盧瓦利亞
摘編 | 青青子
“東方學(xué)”的起源:在認(rèn)識(shí)東方的過(guò)程中構(gòu)建東方
1786年,孟加拉高等法院法官和梵文學(xué)者威廉·瓊斯對(duì)孟加拉亞細(xì)亞學(xué)會(huì)做了一次致辭,在致辭中他說(shuō)了這樣一番即將改變歐洲智識(shí)生活面貌的話:
梵語(yǔ),無(wú)論其古體是什么樣子的,它都有著絕妙的結(jié)構(gòu),比希臘語(yǔ)更完美,比拉丁語(yǔ)更豐富,比這兩門(mén)語(yǔ)言中的任何一門(mén)更精致,卻又在詞根、語(yǔ)法形式上與二者極為相似,這種相似不可能出于偶然;的確,它們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任何考察這三門(mén)語(yǔ)言的語(yǔ)文學(xué)家都不由得要相信,這三門(mén)語(yǔ)言可能源于某個(gè)也許現(xiàn)已不復(fù)存在的共同來(lái)源。(Asiatic Researches 1788,引自Poliakov 1974:190)
瓊斯的這番話引發(fā)了全歐洲的“印度熱”,學(xué)者們紛紛到梵語(yǔ)里去尋找甚至比拉丁語(yǔ)和希臘語(yǔ)還要深藏于歷史的歐洲語(yǔ)言的起源。在印度熱過(guò)后,東方學(xué)被牢固確立了,而語(yǔ)言研究也得到了極大的擴(kuò)張。在接下來(lái)的一個(gè)世紀(jì)里,歐洲的民族學(xué)家、語(yǔ)文學(xué)家和歷史學(xué)家將沉迷于東方和印歐語(yǔ)系,因?yàn)檫@些語(yǔ)言看起來(lái)為歐洲文明自己的根源,提供了某種解釋。
瓊斯的這番話是革命性的,因?yàn)楫?dāng)時(shí)既有的對(duì)語(yǔ)言史的構(gòu)想假設(shè),語(yǔ)言發(fā)展是在創(chuàng)世以來(lái)的6000年里發(fā)生的,希伯來(lái)語(yǔ)是源語(yǔ)言,而其他語(yǔ)言則是通過(guò)一個(gè)墮落的過(guò)程發(fā)展出來(lái)的。瓊斯的宣言引入了一種新的對(duì)語(yǔ)言史的構(gòu)想,但因?yàn)檎Z(yǔ)言是如此深刻地隱含在關(guān)于民族和文化認(rèn)同的考慮之中,于是乎,“真正的和有用的語(yǔ)言科學(xué),也就被瘋狂的‘種族人類(lèi)學(xué)’學(xué)說(shuō)給吞沒(méi)了”(Poliakov 1974:193)。語(yǔ)言和認(rèn)同的關(guān)聯(lián),特別是語(yǔ)言的多樣性和種族認(rèn)同的多樣性的關(guān)聯(lián),引出了民族學(xué)這門(mén)學(xué)科,也就是現(xiàn)代人類(lèi)學(xué)的前身。
按薩義德的說(shuō)法,東方學(xué)主要是一種定義和“定位”歐洲的他者的方式。但作為一組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學(xué)科,東方學(xu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關(guān)乎歐洲本身,并以圍繞民族特性、種族與語(yǔ)言起源為核心的論證為中樞。因此,對(duì)東方語(yǔ)言、歷史和文化的詳盡和細(xì)致的考察,是在這樣一個(gè)語(yǔ)境中進(jìn)行的:其中,歐洲文明的優(yōu)越性和重要性是不受質(zhì)疑的。這就是那種很快就被富有影響力的學(xué)者生產(chǎn)的神話、意見(jiàn)、道聽(tīng)途說(shuō)和成見(jiàn)認(rèn)為是已被接受的真理的話語(yǔ)的力量之所在。比如說(shuō),影響力很大的法國(guó)與文學(xué)家和歷史學(xué)家歐內(nèi)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就可以自信地宣稱(chēng)“每個(gè)人,無(wú)論多么不熟悉我們時(shí)代的事務(wù),都會(huì)清楚地看到,實(shí)際上,信穆罕默德教的國(guó)家是低劣的”(Renan1896:85)。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勒南的受眾,及其共享的文化假設(shè)的性質(zhì):
所有去過(guò)東方或非洲的人都會(huì)震驚于此:真正的信徒頭上的種種鐵箍致命地限制了他的心智,使之在知識(shí)面前把自己完全地封閉起來(lái)。(Renan 1896:85)
這樣的論斷背后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像勒南,以及語(yǔ)文學(xué)家與種族理論家阿圖爾·高比諾伯爵(Count Arthur Gobineau,1816—1882)那樣的作家的廣泛流行給人們帶來(lái)的自信。但在更深的層次上說(shuō),這些作家本身也是歐洲對(duì)世界大多數(shù)其他地方通過(guò)經(jīng)濟(jì)和軍事來(lái)維持的不受質(zhì)疑的支配的產(chǎn)物。通過(guò)這些像勒南的話那樣的陳述,東方學(xué)知識(shí)的“生產(chǎn)”,變成了對(duì)各種假設(shè)和信念的持續(xù)的、不受批判的“再生產(chǎn)”。如此,1908年,極為依賴(lài)像勒南那樣的作家的克拉默勛爵才能夠?qū)懙溃瑲W洲人“受過(guò)訓(xùn)練的才智像機(jī)械一樣工作”,而東方人的心智,則“像他們?nèi)绠?huà)的街道一樣,在對(duì)稱(chēng)方面極其欠缺”(Said 1978a:38)。歐洲的優(yōu)越的“秩序”、“理性”和“對(duì)稱(chēng)”和非·歐洲的低劣的“無(wú)序”、“非理性”和“原始主義”是自我肯定的規(guī)范,而形形色色的東方學(xué)學(xué)科就散布于其中。但給這些學(xué)科以其動(dòng)力和緊迫性的(至少在一開(kāi)始的時(shí)候),是解釋歐洲與其東方祖先之間的明顯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的需要。“東方”的意思,大概就是我們今天說(shuō)的“中東”,包括各種“閃族”語(yǔ)言和社會(huì),以及南亞的社會(huì),因?yàn)檫@些社會(huì)與印歐語(yǔ)言的發(fā)展和傳播最為相關(guān),盡管就像薩義德指出的那樣,東方學(xué)家也傾向于區(qū)分在古印度的“好的”東方跟在今天的亞洲和北非的“壞的”東方(Said 1978a:99)。
對(duì)印歐語(yǔ)系的識(shí)別,在世界史上引發(fā)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它不僅擾亂了常規(guī)的語(yǔ)言史概念,還引起了一個(gè)世紀(jì)的語(yǔ)文學(xué)爭(zhēng)論,但隨著語(yǔ)言和種族的合流,它很快就生成了各種關(guān)于種族的起源與發(fā)展的理論。在不同時(shí)代被稱(chēng)為“雅弗族”語(yǔ)言(得名于諾亞的兒子雅弗,區(qū)別于源于諾亞的另外兩個(gè)兒子閃和含的“閃族”語(yǔ)言和“含族”語(yǔ)言)或“印度-日耳曼”語(yǔ)言的印歐語(yǔ)系開(kāi)始被稱(chēng)為“雅利安語(yǔ)”——因?yàn)槿藗冋J(rèn)為,它們起源于亞洲的雅利湖附近。1819年,通過(guò)德國(guó)哲學(xué)家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的努力,“雅利安”這個(gè)術(shù)語(yǔ)獲得了廣泛的權(quán)威(Poliakov 1974:193)。這個(gè)術(shù)語(yǔ)變成了一個(gè)接近歐洲國(guó)家之核心的觀念——獨(dú)立的語(yǔ)言意味著獨(dú)立的種族/民族起源——的象征。19世紀(jì)初,在用雅利安種族的神話來(lái)激勵(lì)德意志青年的時(shí)候,施萊格爾的修辭啟動(dòng)了一個(gè)最終導(dǎo)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大屠殺的進(jìn)程。因此,這個(gè)原本有統(tǒng)一有著廣泛文化差異的各族人民——印歐語(yǔ)言社群,多樣如印度人、波斯人、條頓人和盎格魯-薩克遜人那樣的人民——之潛能的概念,在滿(mǎn)足歐洲人根深蒂固的種族自負(fù)的同時(shí),變成了最咄咄逼人的種族極化發(fā)展的根源。
把東方學(xué)單純視為19世紀(jì)現(xiàn)代帝國(guó)主義發(fā)展的產(chǎn)物的做法是很有誘惑力的,因?yàn)闅W洲對(duì)東方的控制,的確要求它為自己在文化和經(jīng)濟(jì)上的支配給出一個(gè)智識(shí)上的理由。但話語(yǔ)是被——我們可以這樣說(shuō)——“多因素決定的”(overdetermined):也就是說(shuō),許多不同的因素都對(duì)歷史上的這個(gè)時(shí)候的這個(gè)特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xiàn),而新興的歐洲國(guó)家的帝國(guó)主義,只是這些因素中的一個(gè)(盡管也是顯著的一個(gè))。這些影響的支流也隨國(guó)家而變,比如說(shuō),英國(guó)的工業(yè)支配及其殖民占有的政治經(jīng)濟(jì);法國(guó)革命后的民族命運(yùn)感;德國(guó)條頓人社群持續(xù)了數(shù)個(gè)世紀(jì)之久的對(duì)血統(tǒng)的重視。所有這些合在一起,共同生產(chǎn)出一種研究東方文化的激情,后者也見(jiàn)證了像民族學(xué)、人類(lèi)學(xué)、古生物學(xué)和語(yǔ)文學(xué)那樣的新自然與人文科學(xué)學(xué)科的誕生,以及像歷史學(xué)和地理學(xué)那樣的既有學(xué)科的變形或形式化。東方學(xué)包含的智識(shí)學(xué)科也遠(yuǎn)遠(yuǎn)不是鐵板一塊的,相反,這些學(xué)科的多樣性,主要的歐洲國(guó)家不同的文化史對(duì)它們的“多因素決定”意味著,東方學(xué)也發(fā)展出了不同的智識(shí)風(fēng)格。
但盡管東方學(xué)學(xué)科是復(fù)雜而多樣的,東方學(xué)學(xué)者的研究也都是在特定的規(guī)范內(nèi)操作的,比如說(shuō)這樣的假設(shè)——西方文明是歷史發(fā)展的頂點(diǎn)。因此,東方學(xué)的分析,幾乎總會(huì)進(jìn)一步肯定東方社會(huì)的“原始”、“原初”、“異域”和“神秘”的性質(zhì),并時(shí)常斷定印歐語(yǔ)系的“非-歐洲”分支的墮落。在這方面,東方學(xué)盡管助長(zhǎng)了很多學(xué)科,卻可以被當(dāng)作福柯所說(shuō)的“話語(yǔ)”來(lái)看:一個(gè)連貫一致、邊界分明的社會(huì)知識(shí)領(lǐng)域;一個(gè)人們借以認(rèn)識(shí)世界的陳述構(gòu)成的系統(tǒng)。
話語(yǔ)中有一些不成文的(有時(shí)還是無(wú)意識(shí)的)定義什么能說(shuō)、什么不能說(shuō)的規(guī)則,東方學(xué)話語(yǔ)也有許多這樣的在成規(guī)、習(xí)慣、預(yù)期和假設(shè)的領(lǐng)域運(yùn)作的規(guī)則。在一切獲取關(guān)于世界的知識(shí)的嘗試中,被認(rèn)識(shí)的東西,在極大程度上是為它被認(rèn)識(shí)的方式所決定的;一門(mén)學(xué)科的規(guī)則,決定了人們能夠從中獲得的是何種知識(shí),而這些規(guī)則的強(qiáng)大及其不被說(shuō)出的性質(zhì)也表明,學(xué)術(shù)學(xué)科是原型形式的話語(yǔ)。但在這些規(guī)則貫穿多個(gè)學(xué)科,提供限定此類(lèi)知識(shí)之生產(chǎn)的邊界的時(shí)候,那種言說(shuō)和思考的智識(shí)習(xí)慣就變成了一種像東方學(xué)那樣的話語(yǔ)。這種支持東方學(xué)的話語(yǔ)連貫性的論證,是薩義德對(duì)現(xiàn)象的分析的關(guān)鍵,也是他的論證的說(shuō)服力的來(lái)源。歐洲的知識(shí),通過(guò)不斷地在東方學(xué)話語(yǔ)內(nèi)建構(gòu)它的對(duì)象,才得以維持其對(duì)該對(duì)象的霸權(quán)。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方學(xué)這個(gè)復(fù)雜現(xiàn)象的一個(gè)面向上,使薩義德能夠把東方學(xué)闡述為文化支配機(jī)制的最深刻的例子之一,闡述為帝國(guó)的控制,以及今天也繼續(xù)影響著當(dāng)代生活的那種控制的過(guò)程的轉(zhuǎn)喻。因此,《東方學(xué)》的核心是展示知識(shí)與權(quán)力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因?yàn)闁|方學(xué)話語(yǔ)在“認(rèn)識(shí)”東方的過(guò)程中建構(gòu)和支配了東方。
《東方學(xué)》的在世性:以“東方人”的視點(diǎn)逆轉(zhuǎn)話語(yǔ)的“目光”
《東方學(xué)》是一部毫不掩飾的政治的作品。它的目標(biāo)不是研究那一系列的學(xué)科,也不是細(xì)致地闡述東方學(xué)的歷史或文化的起源,而毋寧說(shuō)是逆轉(zhuǎn)話語(yǔ)的“目光”,從一個(gè)“東方人”的視點(diǎn)來(lái)分析它——“清點(diǎn)那種文化在東方主體上留下的痕跡……那種文化的支配,是所有東方人的生活中的一個(gè)強(qiáng)力的事實(shí)”(Said 1978a:25)。何以薩義德這位著名的美國(guó)學(xué)者能夠聲稱(chēng)自己是一個(gè)“東方人”這件事情,再次重復(fù)了貫穿他的作品的那個(gè)反復(fù)出現(xiàn)的矛盾。但他在美國(guó)(在美國(guó),“東方”意指危險(xiǎn)和威脅)的生活經(jīng)驗(yàn),是《東方學(xué)》的在世性的來(lái)源。這本書(shū)的來(lái)歷展示了東方學(xué)話語(yǔ)的深刻影響,因?yàn)樗苯映鲎砸粋€(gè)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在西方的“令人沮喪的”生活。
的確,網(wǎng)住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種族主義、文化的陳詞濫調(diào)、政治的帝國(guó)主義、非人化的意識(shí)形態(tài)之網(wǎng)是很強(qiáng)的,每一個(gè)巴勒斯坦人都會(huì)感受到這張網(wǎng)獨(dú)有的令人筋疲力盡的命運(yùn)……因此,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創(chuàng)造“東方”并在某種意義上使他們非人化的知識(shí)與權(quán)力的網(wǎng)結(jié),并不完全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問(wèn)題。它也是一個(gè)有一些非常明顯的重要性的智識(shí)的問(wèn)題。(Said 1978a:27)
如我們所見(jiàn),《東方學(xué)》是薩義德自己“獨(dú)有的令人筋疲力盡的命運(yùn)”的果實(shí)。在這本書(shū)中,一個(gè)在美國(guó)生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利用他移居的教授位置,來(lái)分辨文化霸權(quán)的維持方式。他說(shuō),他的意圖是挑釁,并因此而刺激出“一種新的,和東方打交道的方式”(Said 1978a:28)。的確,如果這個(gè)“東方”和“西方”的二元對(duì)立完全消失的話,那么“我們就會(huì)在威爾士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píng)家雷蒙德·威廉斯所謂的對(duì)‘固有的支配模式’的‘忘學(xué)’(unlearning)的過(guò)程中,稍微往前走幾步”(Said 1978a:28)。
薩義德自己的認(rèn)同建構(gòu)工作鞏固了《東方學(xué)》背后的激情。這本書(shū)的智識(shí)力量來(lái)自它對(duì)各種學(xué)科在特定連貫的話語(yǔ)限度內(nèi)運(yùn)作的方式的充滿(mǎn)靈感的、持續(xù)專(zhuān)注的分析,但這本書(shū)的文化的,也許甚至是情感的力量,則來(lái)自其“在世的”直接性,來(lái)自這一點(diǎn):生產(chǎn)它的,是這樣一個(gè)作家——他的認(rèn)同部分地是為這種話語(yǔ)所建構(gòu)的,并且他直到今天都還能感覺(jué)到東方學(xué)“知識(shí)”的影響。在智識(shí)辯論中,激情可能是一個(gè)令人困惑的、無(wú)反思的元素,而盡管激情無(wú)疑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東方學(xué)》的流行,但是許多(因?yàn)檫@本書(shū)中的激情元素而)拒絕考慮這本書(shū)的在世性的批評(píng)家,也往往因此而限制了他們對(duì)這本書(shū)的意義的認(rèn)識(shí)。比如說(shuō),這本書(shū)的一位阿拉伯評(píng)論者巴希姆·木薩拉姆(Basim Musallam)指出,一個(gè)充滿(mǎn)敵意的批評(píng)家,學(xué)者邁克爾·魯斯塔姆(Michael Rustum)“就是以一個(gè)自由人和一個(gè)自由社會(huì)的一員;一個(gè)說(shuō)阿拉伯語(yǔ)的,還獨(dú)立自治的奧斯曼國(guó)家的敘利亞公民的身份寫(xiě)作的”(Said 1995a:337)。但愛(ài)德華·薩義德“沒(méi)有公認(rèn)的認(rèn)同”,木薩拉姆說(shuō),“他的人民還在爭(zhēng)論中。有可能,愛(ài)德華·薩義德和他那一代人立足的基礎(chǔ),并不比邁克爾·魯斯塔姆的敘利亞的被毀滅的社會(huì)的殘余更堅(jiān)實(shí),有可能他們依憑的只是記憶”。木薩拉姆指出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寫(xiě)這本書(shū)的不只是隨便的一個(gè)‘阿拉伯人’,還是一個(gè)有特定的背景和經(jīng)驗(yàn)的阿拉伯人。”(Musallam,引自Said 1995a:3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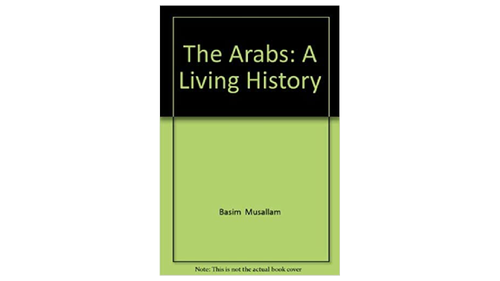
巴希姆·木薩拉姆的《阿拉伯人》
但要說(shuō)薩義德的意圖只是在維護(hù)一種(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將把他和其他被殖民的主體祛除到殖民化的經(jīng)驗(yàn)和遺產(chǎn)外——的同時(shí)發(fā)泄自己的憤怒,那就太過(guò)于簡(jiǎn)化了。這樣的立場(chǎng),對(duì)他關(guān)于公共知識(shí)分子的“世俗”角色的看法來(lái)說(shuō)是可惡的——在薩義德看來(lái),公共知識(shí)分子是要開(kāi)拓空間和跨越邊界,努力“對(duì)權(quán)力說(shuō)真話”的。薩義德接過(guò)弗朗茨·法農(nóng)未完成的計(jì)劃,從一種指責(zé)的政治,走向了一種解放的政治。然而,正如他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盡管他發(fā)出了關(guān)于在他眼中他的作品將致力于什么——?jiǎng)?chuàng)造一種非強(qiáng)制性、非支配性和非本質(zhì)主義的知識(shí)——的聲明,但“更經(jīng)常的情況卻是”《東方學(xué)》“被認(rèn)為是某種對(duì)次屬地位——大地上受苦的人們回嘴了——的肯定,而不是一種對(duì)用知識(shí)來(lái)促進(jìn)自己的權(quán)力的多元文化的批判”(Said 1995a:336)。
在《東方學(xué)》出版之前,“東方學(xué)”這個(gè)術(shù)語(yǔ)本身已經(jīng)不是流行的用語(yǔ)了,但在1970年代末的時(shí)候,它又獲得了充滿(mǎn)活力的新生。現(xiàn)代東方研究的各門(mén)學(xué)科,盡管都很復(fù)雜,卻都不可避免地被灌輸了各種傳統(tǒng)的對(duì)東方(特別是中東)的性質(zhì)的再現(xiàn),以及各種支撐東方學(xué)話語(yǔ)的假設(shè)。盡管薩義德也哀嘆,有時(shí)人們對(duì)《東方學(xué)》的挪用過(guò)于恣意,但無(wú)疑,《東方學(xué)》的的確確對(duì)普遍而言的社會(huì)理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到1995年的時(shí)候,《東方學(xué)》已經(jīng)變成一本出人意料地“廢除”了它的作者的“集體的書(shū)”了(Said 1995a:300)。你還可以補(bǔ)充說(shuō),就對(duì)東方學(xué)策略的分析在識(shí)別帝國(guó)文化的各種特定的話語(yǔ)和文化操作上一直是有用的而言,《東方學(xué)》也是一本持續(xù)成長(zhǎng)的書(shū)。因?yàn)檫@些分析主要處理的,是再現(xiàn)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以及權(quán)力的再現(xiàn)(盡管它們從性質(zhì)上說(shuō)是刻板的印象和夸張的描述)是怎樣變成“真實(shí)的”和為人們所接受的再現(xiàn)的。
東方學(xué)的范圍:東方作為附著于歐洲的舞臺(tái)劇場(chǎng)
薩義德的論證的核心在于知識(shí)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聯(lián),1910年首相阿瑟·貝爾福對(duì)英國(guó)占領(lǐng)埃及的辯護(hù)明確地展示了這點(diǎn)。當(dāng)時(shí),貝爾福宣告:“我們對(duì)埃及文明的認(rèn)識(shí),超過(guò)了我們對(duì)其他任何國(guó)家的認(rèn)識(shí)”(Said 1978a:32)。對(duì)貝爾福來(lái)說(shuō),知識(shí)不僅意味著從起源開(kāi)始全面概述一個(gè)文明,也意味著有能力那么做。“有這樣程度的對(duì)(像埃及)這樣的東西的認(rèn)識(shí),也就是支配它,對(duì)它有權(quán)威……因?yàn)槲覀冎浪谀撤N意義上,也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存在著”(Said 1978a:32)。貝爾福的言論的前提,清晰地展示了知識(shí)和支配是怎樣攜手并進(jìn)的:
英國(guó)知道埃及;埃及就是英國(guó)知道的那個(gè)樣子;英國(guó)知道埃及不可能自治;英國(guó)通過(guò)占領(lǐng)埃及肯定了這點(diǎn);對(duì)埃及人來(lái)說(shuō),埃及就是英國(guó)已經(jīng)占領(lǐng)了的、現(xiàn)在治理著的那個(gè)樣子;因此,外國(guó)的占領(lǐng)也就變成了當(dāng)代埃及文明的“基礎(chǔ)本身”。(Said 1978a:34)
但只看到東方學(xué)是殖民統(tǒng)治的合理化解釋?zhuān)褪呛鲆暳诉@個(gè)事實(shí),即殖民主義事先就在東方學(xué)那里得到了正名(Said 1978a:39)。世界的東西方之分已經(jīng)醞釀了好幾個(gè)世紀(jì),它表達(dá)了一個(gè)根本的兩分,而人們就是在這個(gè)兩分的基礎(chǔ)上和東方打交道的。但在這個(gè)兩分中,只有一方有權(quán)力決定東方和西方的現(xiàn)實(shí)可能是什么樣子的。因?yàn)殛P(guān)于東方的知識(shí)是從這種文化力量中生成出來(lái)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創(chuàng)造了東方、東方人及其世界”(Said 1978a:40)。這一論斷把我們直接引入了《東方學(xué)》的核心,結(jié)果,也讓我們看到了它引起的大量爭(zhēng)論的根源。對(duì)薩義德來(lái)說(shuō),東方和東方人是歐洲人借以認(rèn)識(shí)他們的各色學(xué)科直接建構(gòu)出來(lái)的。這看起來(lái)一方面把一個(gè)極其復(fù)雜的歐洲現(xiàn)象縮小為一個(gè)簡(jiǎn)單的、權(quán)力與帝國(guó)關(guān)系的問(wèn)題,但另一方面又沒(méi)有為東方的自我再現(xiàn)提供任何空間。
薩義德指出,東方學(xué)研究的劇增,在時(shí)間上與歐洲空前的擴(kuò)張的時(shí)期契合:從1815年到1914年。他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把注意力集中在現(xiàn)代東方學(xué)的開(kāi)端上,我們可以看到東方學(xué)的政治性質(zhì)。而這個(gè)開(kāi)端,不在于威廉·瓊斯對(duì)語(yǔ)言學(xué)正統(tǒng)的擾亂,而在于1798年拿破侖對(duì)埃及的入侵,這一入侵“從許多角度來(lái)看,就是一個(gè)顯然更強(qiáng)大的文化對(duì)另一個(gè)文化的真正科學(xué)的占有的模型本身”(Said 1978a:42)。但關(guān)鍵的事實(shí)是,東方學(xué),就其所有的支流而言,開(kāi)始對(duì)關(guān)于東方的思想強(qiáng)加限制。甚至像古斯塔夫·福樓拜、熱拉爾·德·奈瓦爾或沃爾特·斯科特爵士那樣厲害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在關(guān)于東方他們能經(jīng)驗(yàn)到什么、能說(shuō)什么上也受到了限制。因?yàn)椤皷|方學(xué)說(shuō)到底是一種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政治想象,其結(jié)構(gòu)是促進(jìn)熟悉的(歐洲,西方,‘我們’)和陌生的(東方學(xué)的東方,世界的東方,‘他們’)之間的差異的”(Said 1978a:43)。它起到這樣的作用,是因?yàn)闁|方學(xué)話語(yǔ)的智識(shí)成就服務(wù)于帝國(guó)權(quán)力的巨大的等級(jí)網(wǎng)絡(luò),并且本身也受制于這個(gè)網(wǎng)絡(luò)。
話語(yǔ)出現(xiàn)的關(guān)鍵,是一個(gè)被稱(chēng)為“東方”的東西的想象的存在,這個(gè)“東方”是在薩義德所謂的“想象的地理學(xué)”中形成的,因?yàn)椴皇钦f(shuō)我們可以發(fā)展出一門(mén)被稱(chēng)為“東方研究”的學(xué)科。很簡(jiǎn)單,東方這個(gè)觀念存在是為了定義什么是歐洲的。“一個(gè)像西方和東方之分那樣的大的區(qū)分,引出了其他更小的區(qū)分”(Said 1978a:58)而從希羅多德和亞歷山大大帝以降的作家、旅行家、士兵、政治家的經(jīng)驗(yàn),則變成了“人們經(jīng)驗(yàn)西方的透鏡,它們塑造了東方與西方遭遇的語(yǔ)言、對(duì)此遭遇的認(rèn)識(shí)以及遭遇的形式”(Said 1978a:58)。聚合這些經(jīng)驗(yàn)的是一種共享的、對(duì)某種“他者的”、被命名為“東方”的東西的感覺(jué)。這個(gè)對(duì)東方學(xué)的二元性的分析,一直是這本書(shū)遭到的許多批評(píng)的來(lái)源,因?yàn)樗雌饋?lái)是在暗示存在一個(gè)歐洲或一個(gè)西方(一個(gè)“我們”),這個(gè)一元的歐洲或西方或“我們”建構(gòu)了東方。但如果我們把這個(gè)同質(zhì)化看作東方學(xué)話語(yǔ),至少是含蓄地簡(jiǎn)化世界的方式,而不把它看作世界真實(shí)存在的方式;把它看作一種普遍的態(tài)度與形形色色的學(xué)科和智識(shí)分支關(guān)聯(lián)的方式(盡管這些學(xué)科和智識(shí)分支的主題和操作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我們就可以理解到這種無(wú)處不在的思考和所謂的東方學(xué)的習(xí)慣的話語(yǔ)力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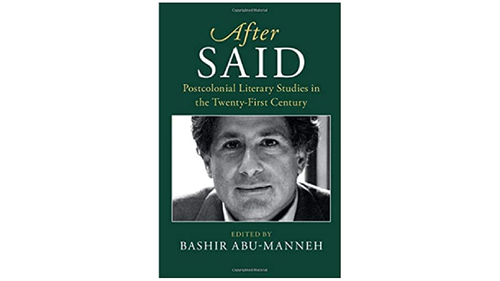
巴希爾·艾布-曼內(nèi)赫編纂的《薩義德之后》
我們可以通過(guò)劇場(chǎng)的比喻,來(lái)闡明我們理解這種二元的、刻板印象式的認(rèn)識(shí)中的那個(gè)被稱(chēng)為“東方”的“他者”的方式。作為一個(gè)學(xué)識(shí)領(lǐng)域的東方學(xué)這個(gè)觀念暗示著一個(gè)封閉的空間,而再現(xiàn)這個(gè)觀念則是劇場(chǎng)式的:東方學(xué)的東方是一個(gè)舞臺(tái),而整個(gè)世界的東方就被限制在這個(gè)舞臺(tái)上。
在這個(gè)舞臺(tái)上將出現(xiàn)這樣的人物,他們來(lái)自某個(gè)更大的整體,而他們的作用,正是代表/再現(xiàn)那個(gè)整體。因此,東方看起來(lái)不是一個(gè)在熟悉的歐洲世界之外的、無(wú)限的(地理)延伸,而毋寧說(shuō)是一個(gè)封閉的場(chǎng)域,一個(gè)附著于歐洲的劇場(chǎng)舞臺(tái)。(Said 1978a:63)
想象的地理學(xué)給了為對(duì)東方的理解所特有的一套語(yǔ)匯、一種代表/再現(xiàn)性的話語(yǔ)以合法性,而這套語(yǔ)匯和話語(yǔ),也就變成了人們認(rèn)識(shí)東方的唯一方式。東方學(xué)因此也就變成了“徹底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種形式,通過(guò)它,東方的一個(gè)面向被一個(gè)詞或短語(yǔ)給固定了,“接著,這個(gè)詞或短語(yǔ)也就被認(rèn)為獲得了現(xiàn)實(shí),或者更簡(jiǎn)單地,它本身就是現(xiàn)實(shí)”(Said 1978a:72)。
薩義德的分析的焦點(diǎn),是由他所看到的19世紀(jì)東方學(xué)的飛速發(fā)展和歐洲帝國(guó)主義支配的興起之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提供的。通過(guò)他賦予1798年拿破侖入侵埃及這個(gè)事件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分析的政治導(dǎo)向。盡管不是19世紀(jì)初席卷歐洲的東方學(xué)的開(kāi)端,但拿破侖的計(jì)劃,的確展示了學(xué)術(shù)知識(shí)和政治野心之間的最有意識(shí)的聯(lián)姻。當(dāng)然,1870年代印度總督瓦倫·黑斯廷斯做出的在梵法基礎(chǔ)上組織印度的法院系統(tǒng)的決定,為幫助翻譯梵文的威廉·瓊斯的發(fā)現(xiàn)鋪平了道路。這表明,任何種類(lèi)的知識(shí)都是有位置的,其力量也來(lái)自它所處的政治現(xiàn)實(shí)。但拿破侖的戰(zhàn)略——說(shuō)服埃及人,他是代表伊斯蘭而戰(zhàn)的,而不是要反對(duì)伊斯蘭——利用了法國(guó)學(xué)者所能搜羅的一切可用的、關(guān)于古蘭與伊斯蘭社會(huì)的知識(shí),它全面地演示了知識(shí)的策略和戰(zhàn)略力量。
在離開(kāi)埃及后,拿破侖給他的副官克雷貝爾嚴(yán)格的指示:永遠(yuǎn)通過(guò)東方學(xué)家和他們可以爭(zhēng)取到的伊斯蘭的宗教領(lǐng)袖來(lái)管理埃及(Said 1978a:82)。根據(jù)薩義德,這次遠(yuǎn)征的后果是深刻的。“相當(dāng)確切地說(shuō),占領(lǐng)引出了整個(gè)現(xiàn)代的對(duì)東方的經(jīng)驗(yàn):人們是從拿破侖在埃及建立的話語(yǔ)宇宙內(nèi)部出發(fā)來(lái)詮釋這種經(jīng)驗(yàn)的。”(Said 1978a:87)薩義德說(shuō),在拿破侖之后,東方學(xué)的語(yǔ)言本身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它的描述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升級(jí)了,在升級(jí)后,它不再只是一種再現(xiàn)風(fēng)格,而變成了一種語(yǔ)言,也變成了一種創(chuàng)造的手段”(Said 1978a:87),其象征是充滿(mǎn)雄心的對(duì)蘇伊士運(yùn)河的建造。像這樣的主張展示了,為什么薩義德的論證如此有說(shuō)服力,以及為什么在1970年代的時(shí)候它能夠抓住批評(píng)家們的想象。更細(xì)致的考察將揭示,最密集的東方學(xué)研究大多是在像德國(guó)那樣幾乎沒(méi)有什么殖民地的國(guó)家展開(kāi)的。更廣泛的分析也會(huì)揭示,東方學(xué)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再現(xiàn)風(fēng)格。但拿破侖的遠(yuǎn)征給東方學(xué)家的工作指出了一個(gè)明確無(wú)誤的方向,后者不但在歐洲和中東史上,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筆還在持續(xù)傳承的遺產(chǎn)。
從根本上說(shuō),東方學(xué)會(huì)有這樣的力量和這樣無(wú)與倫比的生產(chǎn)能力,是因?yàn)樗鼜?qiáng)調(diào)文本性,它傾向于從先前寫(xiě)就的文本獲得的知識(shí)的框架內(nèi)介入現(xiàn)實(shí)。東方學(xué)是密集的多層次寫(xiě)作,這些寫(xiě)作號(hào)稱(chēng)要直接介入它們的對(duì)象,但事實(shí)上卻是在回應(yīng)先前的寫(xiě)作,在先前的寫(xiě)作的基礎(chǔ)上建造。這種文本的態(tài)度一直延續(xù)至今,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反對(duì)以色列人的定居和對(duì)他們的土地的占領(lǐng)的話,那么,這不過(guò)是“伊斯蘭的回歸”,或者說(shuō),就像一個(gè)著名的當(dāng)代東方學(xué)家解釋的那樣,不過(guò)是伊斯蘭的一個(gè)在7世紀(jì)時(shí)被奉為神圣的原則,即伊斯蘭對(duì)非伊斯蘭的人民的反對(duì)而已。(Said 1978a:107)
東方學(xué)的話語(yǔ):一種權(quán)力/知識(shí)的表現(xiàn)
我們最好從福柯的角度,把東方學(xué)看作一種話語(yǔ):一種權(quán)力/知識(shí)的表現(xiàn)。薩義德說(shuō),在不把東方學(xué)當(dāng)作一種話語(yǔ)來(lái)考察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理解“后啟蒙時(shí)期,歐洲文化借以在政治的、社會(huì)學(xué)的、軍事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科學(xué)的、想象的意義上管理——甚至是生產(chǎn)——東方的那套極為系統(tǒng)的規(guī)訓(xùn)”(Said 1978a:3)。
接著我們先前看到的話語(yǔ)概念往后說(shuō),殖民話語(yǔ)是一個(gè)由關(guān)于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關(guān)于殖民的列強(qiáng),關(guān)于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人們可以做出的陳述構(gòu)成的系統(tǒng)。它是關(guān)于那個(gè)世界——殖民化的行動(dòng)就是在這個(gè)世界中發(fā)生的——的知識(shí)和信念的系統(tǒng)。
盡管它是在殖民者的社會(huì)和文化中生成的,但它卻變成了這樣一種話語(yǔ):被殖民者也會(huì)在這種話語(yǔ)內(nèi)看待自己(就像在非洲人接受帝國(guó)對(duì)他們的看法,認(rèn)為自己是“直覺(jué)的”和“感性的”,并斷定自己與“理性的”和“非感性的”歐洲人不同的時(shí)候)。至少,它也在被殖民者的意識(shí)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深刻的沖突,因?yàn)樗c其他關(guān)于世界的知識(shí)是沖突的。
作為一種話語(yǔ),東方學(xué)被賦予了學(xué)院、制度和政府的權(quán)威;這個(gè)權(quán)威,把話語(yǔ)提高到一個(gè)重要的、尊貴的層級(jí)上;而話語(yǔ)因此而獲得的重要性和特權(quán),又保障了它與“真理”的等同。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后,東方學(xué)學(xué)科創(chuàng)造的知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出一種話語(yǔ)——而“真正為從它(東方學(xué))那里生產(chǎn)出來(lái)的文本負(fù)責(zé)的,不是某位既定的作者的原創(chuàng)性,而是它的物質(zhì)的在場(chǎng)或重量”(Said 1978a:94)。薩義德認(rèn)為,通過(guò)這種話語(yǔ),西方的文化制度要為那些“他者”、東方人的(被)創(chuàng)造負(fù)責(zé),而這些他者和東方與西方的差異,又幫助建立了歐洲賴(lài)以確立自己的認(rèn)同的那個(gè)二元對(duì)立。支撐這一界分的,是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那條“與其說(shuō)是一個(gè)自然的事實(shí)不如說(shuō)是一個(gè)人類(lèi)生產(chǎn)的事實(shí)”的界線(Said 1985:2)。處在對(duì)像“東方”那樣的實(shí)體的建構(gòu)核心的,是地理的想象。它要求維持嚴(yán)格的邊界,以區(qū)分東方和西方。因此,通過(guò)這個(gè)過(guò)程,它們都獲得了使那個(gè)區(qū)域“東方化”的能力。
當(dāng)然,東方學(xué)的一個(gè)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在這個(gè)關(guān)系中,前者(即西方)占優(yōu)勢(shì)。這個(gè)權(quán)力和關(guān)于東方的知識(shí)的建構(gòu)密切相關(guān)。它之所以會(huì)發(fā)生,是因?yàn)殛P(guān)于“臣屬種族”或“東方人”的知識(shí)使對(duì)他們的管理變得容易和有利可圖;“知識(shí)帶來(lái)權(quán)力,更多的權(quán)力要求更多的知識(shí),如此反復(fù)——信息與控制之間存在一種越來(lái)越有利可圖的辯證”(Said 1978a:36)。
東方學(xué)話語(yǔ)創(chuàng)造的、內(nèi)嵌于東方學(xué)的關(guān)于東方的知識(shí)起到了建構(gòu)一個(gè)次屬于、服從于西方支配的東方和東方人的意象的作用。薩義德說(shuō),關(guān)于東方的知識(shí),因?yàn)槭橇α可傻模砸簿驮谀撤N意義上創(chuàng)造了東方、東方人及其世界。
在克羅默和貝爾福的語(yǔ)言中,東方人被描述為某種你可以審判的(就像在法庭上那樣)、你可以研究和描繪的(就像在學(xué)校的課程里那樣)、你可以規(guī)訓(xùn)的(就像在學(xué)校或監(jiān)獄里那樣)、你可以配圖說(shuō)明的(就像在動(dòng)物園手冊(cè)里那樣)的東西。要點(diǎn)在于,在每一種情況下,東方都被支配的框架給控制和代表/再現(xiàn)了。(Said 1978a:40)
創(chuàng)造作為“他者”的東方是必要的,這樣,西方才可以通過(guò)調(diào)用這樣一個(gè)對(duì)比項(xiàng)來(lái)定義自己,強(qiáng)化自己的認(rèn)同。
東方學(xué)的再現(xiàn)不只得到了像人類(lèi)學(xué)、歷史學(xué)和語(yǔ)言學(xué)那樣的學(xué)術(shù)學(xué)科的強(qiáng)化,也為“達(dá)爾文關(guān)于幸存與自然選擇的論題”所強(qiáng)化(Said 1978a:227)。因此,從東方學(xué)的視角來(lái)看,對(duì)東方的研究,永遠(yuǎn)是從一個(gè)西方人或西方的視點(diǎn)出發(fā)的。根據(jù)薩義德,對(duì)西方人來(lái)說(shuō),
東方永遠(yuǎn)和西方的某一面相像,比如說(shuō),對(duì)一些德國(guó)浪漫主義者來(lái)說(shuō),印度的宗教本質(zhì)上是日耳曼·基督教泛神論的東方版。而東方學(xué)家,則把這個(gè)——他永遠(yuǎn)在把東方從一個(gè)東西轉(zhuǎn)化為另一個(gè)東西——當(dāng)作了自己的工作:他為他自己,為了他自己的文化而做這個(gè)工作。(Said 1978a:67)
這種對(duì)東方的編碼,以及對(duì)東方與西方的比較,最終確保了這點(diǎn):東方的文化和視角被看作一種偏差、一種變態(tài),并因此而獲得一個(gè)低劣的地位。
東方學(xué)話語(yǔ)的一個(gè)本質(zhì)特征是東方和東方人的客體化。它們都被當(dāng)作可被審視和理解的客體來(lái)對(duì)待,而這個(gè)客體化,在“東方”這個(gè)術(shù)語(yǔ)中就得到了確認(rèn)——“東方”包含一整個(gè)地理區(qū)域和一大批人口,比歐洲大許多倍,也比歐洲多樣許多倍。這樣的客體化引出了這樣一個(gè)假設(shè):東方本質(zhì)上是鐵板一塊的,它的歷史是靜止不變的;而實(shí)際上,東方卻是動(dòng)態(tài)的,它的歷史也是活躍的。此外,東方和東方人也被視為被動(dòng)的、無(wú)參與的研究對(duì)象。
不過(guò),就西方的知識(shí)總會(huì)不可避免地引出政治的意義而言,這種建構(gòu)也有一個(gè)獨(dú)特的政治維度。在東方研究的興起和西方帝國(guó)主義的崛起那里,這點(diǎn)得到了最好的例示。19世紀(jì)印度或埃及的英國(guó)人對(duì)那些被他們發(fā)現(xiàn)的、淪為英國(guó)殖民地的國(guó)家發(fā)生了興趣。薩義德指出,這看起來(lái)可能“和說(shuō)所有關(guān)于印度和埃及的學(xué)術(shù)知識(sh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惡心的政治事實(shí)的沾染、印刻和侵犯”截然不同,“但這就是我在這本對(duì)東方學(xué)的研究中要說(shuō)的事情”(Said 1978a:11)。薩義德之所以能這么說(shuō),是因?yàn)樗麍?jiān)信,這種話語(yǔ)是在世的:“任何人文科學(xué)中的知識(shí)生產(chǎn)都不可能忽視或否認(rèn)其作者作為一個(gè)人類(lèi)主體對(duì)他自己的境遇的參與。”(Said 1978a:11)。學(xué)術(shù)知識(shí)被政治和軍事力量“沾染”、“印刻”和“侵犯”這個(gè)觀念不是說(shuō),像德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 1983)指出的那樣,東方學(xué)話語(yǔ)的霸權(quán)影響不是通過(guò)“同意”來(lái)運(yùn)作的。相反,它說(shuō)的是,在殖民主義的語(yǔ)境中,看起來(lái)在道德上持中立態(tài)度的對(duì)知識(shí)的追求,實(shí)際上充滿(mǎn)了帝國(guó)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假設(shè)。“知識(shí)”永遠(yuǎn)是一個(gè)再現(xiàn)的問(wèn)題,而再現(xiàn)又是一個(gè)給意識(shí)形態(tài)概念以具體形式,使特定能指表示特定所指的過(guò)程。支撐這些再現(xiàn)的權(quán)力,與政治力量的運(yùn)作是分不開(kāi)的,即便它是一種不同的權(quán)力,一種更微妙、更具穿透性,也更不可見(jiàn)的權(quán)力。
![《文化與帝國(guó)主義》,[美]愛(ài)德華·W·薩義德著,李琨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3年10月。 《文化與帝國(guó)主義》,[美]愛(ài)德華·W·薩義德著,李琨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3年10月。](/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9/2524467_500x500.png)
《文化與帝國(guó)主義》,[美]愛(ài)德華·W·薩義德著,李琨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3年10月。
因此,權(quán)力的不平衡,不僅存在于帝國(guó)主義的最明顯的特征,存在于它的“野蠻的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和軍事的基本原理”(Said 1978a:12)中,也最為霸權(quán)地存在于它的文化話語(yǔ)中。我們可以在文化領(lǐng)域中識(shí)別被用來(lái)宣傳帝國(guó)主義目標(biāo)的支配霸權(quán)的東方學(xué)研究計(jì)劃。因此,薩義德的方法論是內(nèi)嵌于他所謂的“文本主義”的,“文本主義”允許他把東方設(shè)想為一個(gè)文本的創(chuàng)造。在東方學(xué)的話語(yǔ)中,文本的認(rèn)屬迫使它把西方生產(chǎn)為一個(gè)區(qū)別于作為知識(shí)的客體的,以及不可避免地從屬的“他者”的權(quán)力的場(chǎng)所和中心。東方學(xué)文本的隱藏的政治功能,是它的在世性的一個(gè)特征,而薩義德的計(jì)劃,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方作為一個(gè)文本建構(gòu)的建立過(guò)程上。他對(duì)分析隱藏在東方學(xué)文本中的東西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展示東方學(xué)家是怎樣“使東方說(shuō)話,描述東方,為西方、對(duì)西方說(shuō)明它的神秘”的(Said 1978a:20-1)。
再現(xiàn)問(wèn)題是理解話語(yǔ)——知識(shí)總是在話語(yǔ)中建構(gòu)——的關(guān)鍵,因?yàn)樗_義德說(shuō),真實(shí)的再現(xiàn)可不可能都是成問(wèn)題的(Said 1978a:272)。如果所有的再現(xiàn)都內(nèi)嵌于再現(xiàn)者的語(yǔ)言、文化和制度的話,“那么我們必須做好接受這個(gè)事實(shí)的準(zhǔn)備,那就是,再現(xiàn)本身(eoiPSo)就是和除‘真理’外的許多其他東西牽連、交纏、嵌套、交織在一起的,所謂的‘真理’本身也是一種再現(xiàn)”(Said 1978a:272)。那種信念——相信像我們?cè)跁?shū)中發(fā)現(xiàn)的那樣的再現(xiàn),是與真實(shí)的世界對(duì)應(yīng)的——就是薩義德所謂的“文本的態(tài)度”。他指出,法國(guó)哲學(xué)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在《贛第德》和西班牙小說(shuō)家塞萬(wàn)提斯(Cervantes,1547—1616)在《唐吉訶德》中諷刺的,正是這樣的假設(shè):“我們可以在書(shū)本——文本——說(shuō)的東西的基礎(chǔ)上理解生活中蜂擁而來(lái)的、不可預(yù)期的、難題性的混亂,而人類(lèi)就是在這樣的混亂中生活的。”(Said 1978A:93)這確切來(lái)說(shuō),正是在人們以為東方學(xué)的文本意指、再現(xiàn)真理時(shí)發(fā)生的事情:東方被迫沉默,它的現(xiàn)實(shí)被東方學(xué)家揭露。因?yàn)闁|方學(xué)的文本提供了一種對(duì)一個(gè)遙遠(yuǎn)和異域的現(xiàn)實(shí)的熟悉甚至是親近,所以,這些文本本身被賦予極高的地位,并獲得了比它們?cè)噲D描述的客體更大的重要性。薩義德認(rèn)為“這樣的文本不但能夠創(chuàng)造知識(shí),還能夠創(chuàng)造它們看似在描述的現(xiàn)實(shí)”(Said 1978A:94)。結(jié)果,考慮到東方人自己是被禁止說(shuō)話的,所以,創(chuàng)造和描述東方之現(xiàn)實(shí)的,就是這些文本。
東方學(xué)的最新階段,與美國(guó)取代法國(guó)和英國(guó)在世界舞臺(tái)上的地位相應(yīng)。盡管權(quán)力的中心發(fā)生了轉(zhuǎn)移,東方學(xué)的策略也隨之而發(fā)生了變化,但是,東方學(xué)的話語(yǔ),在它的三個(gè)一般模型中一直是穩(wěn)固的。在這個(gè)階段,阿拉伯穆斯林已經(jīng)占據(jù)了美國(guó)流行意象中、社會(huì)科學(xué)中的核心位置。薩義德認(rèn)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椤傲餍械姆撮W族(Anti·Semiti C)的敵意從猶太人轉(zhuǎn)移到了阿拉伯人頭上……因?yàn)檫@個(gè)形象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Said 1978a:286)。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社會(huì)科學(xué)的主導(dǎo)地位意味著,東方學(xué)的衣缽傳到了社會(huì)科學(xué)那里。這些社會(huì)科學(xué)家確保這個(gè)區(qū)域“在概念上被削弱、簡(jiǎn)化為各種‘態(tài)度’、‘趨勢(shì)’、數(shù)據(jù):簡(jiǎn)言之,使之非人化”(Said 1978a:291)。因此,東方學(xué),在它的幾個(gè)不同的階段,都是一種通過(guò)數(shù)代學(xué)者和作家(這些學(xué)者和作家一直享有他們“高人一等”的智慧帶來(lái)的權(quán)力)積累的知識(shí),來(lái)建構(gòu)“東方”的歐洲中心的話語(yǔ)。薩義德的意圖不僅是記錄東方學(xué)的過(guò)度(盡管在這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也是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一種替代性的、更好的學(xué)術(shù)的需要。他認(rèn)識(shí)到,也有許多個(gè)體的學(xué)者在參與這樣的知識(shí)的生產(chǎn)。但他關(guān)心的是東方學(xué)的“行會(huì)傳統(tǒng)”,這個(gè)傳統(tǒng)有能力腐蝕大多數(shù)學(xué)者。他敦促人們?cè)谂c東方學(xué)的支配的斗爭(zhēng)中持續(xù)保持警惕。對(duì)薩義德來(lái)說(shuō),答案是“對(duì)再現(xiàn)、研究他者、種族思想、不加思考和批判地接受權(quán)威和權(quán)威的觀念、知識(shí)分子的社會(huì)·政治角色、懷疑的批判意識(shí)的巨大價(jià)值涉及的東西保持敏感”(Said 1978a:327)。在這里,知識(shí)分子的最高義務(wù),是抵抗那些隱含在東方學(xué)話語(yǔ)傳統(tǒng)中的東西的“神學(xué)”立場(chǎng)的誘惑,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權(quán)力說(shuō)真話、質(zhì)疑和反對(duì)的“世俗”欲望。
編輯:陳姝延
關(guān)鍵詞:東方學(xué) 薩義德 閱讀


